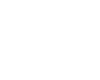在中國人民大學清風學社,一群年輕的清史學人正闊步走在學術的曠野之上。清風拂過,學術的氣息撲面而來,歷史的大門由此打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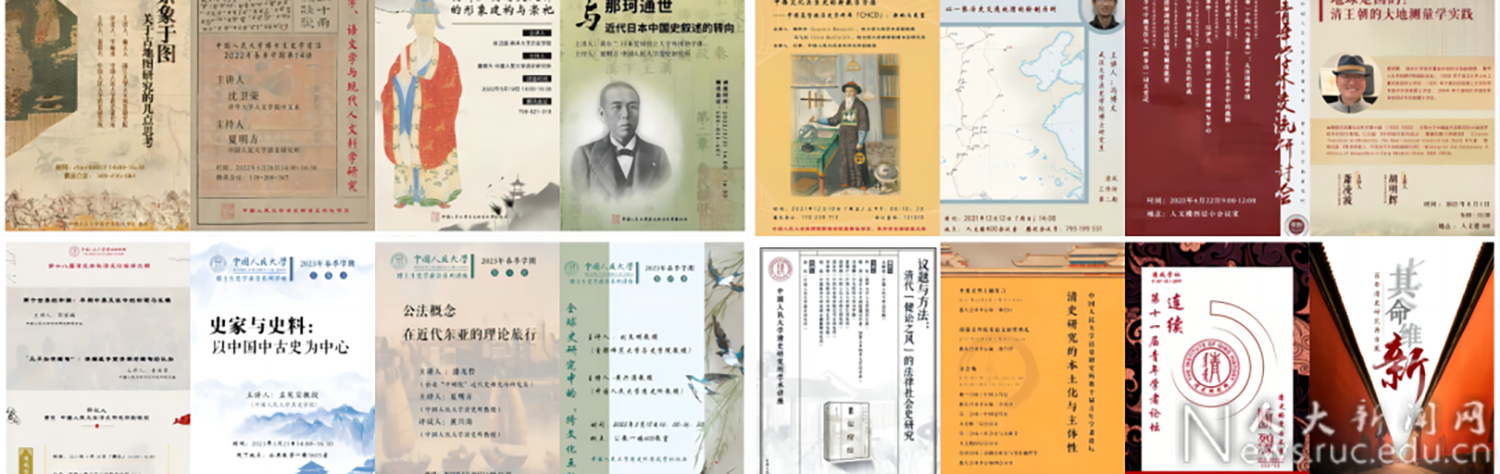
12月的第一個周末,陽光明亮又溫暖,在校園里傾灑而下。
清風學社成員、2021級中國史專業專門史方向博士生尹世奇帶著自己的論文《軍臺“效力贖罪”與清代邊疆治理模式》,出現在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第十三屆青年學者論壇上。
這是他第二次參加論壇,參會的都是來自海內外高校及科研機構的清史領域研究生。

逸夫報告廳內,和尹世奇一樣,這群年輕的清史學人,圍繞“政治與制度”“經濟與地理”“社會與文化”“邊疆與民族”“外交與軍事”等清史研究中的前沿議題,交流、碰撞、激蕩,學術的火花不斷迸發,歷史的藤蔓在滿是好奇的頭腦里瘋狂生長。

在學術之路上同行
對尹世奇來說,這次參會的論文題目熟悉中又帶著幾分陌生。
第一次參會時,他也是寫“軍臺”。
那篇題為《軍臺效力與清代邊疆經營》的學術處女作,在第十二屆青年學者論壇上,收獲了不少“犀利”的意見,有同學說切口太小,有老師說史料還應當進一步豐富完善,還有的同學從社會史、政治史的視角提出了新的觀點。
下來之后,尹世奇一一吸收會上老師和同學們提出的建議和啟發,在導師張永江教授的指導下,論文幾經打磨,數易其稿,最終在2023年第1期的《清史研究》付梓見刊。
“收到稿件錄用通知的那個下午,是我多年求學生涯中最開心的時刻!像一束光,在艱辛的跋涉中,點亮了我的學術熱情。接下來的一整個寒假,我都把頭埋在文獻里,不停地讀文章、寫文章、改文章。”
也正是從這一篇文章開始,尹世奇確定了自己博士階段的研究主題。
兩年多前,尹世奇才剛剛邁進清史的大門,如今,他已有3篇高水平論文發表在《民族研究》《清史研究》等頂尖學術刊物上,在同輩中嶄露頭角。
這樣快的成長,離不開一群人的并肩同行。
他們以史為名,相結于社,是為清風學社。
每兩年一屆的清史研究所青年學者論壇就是由清風學社的同學們組織承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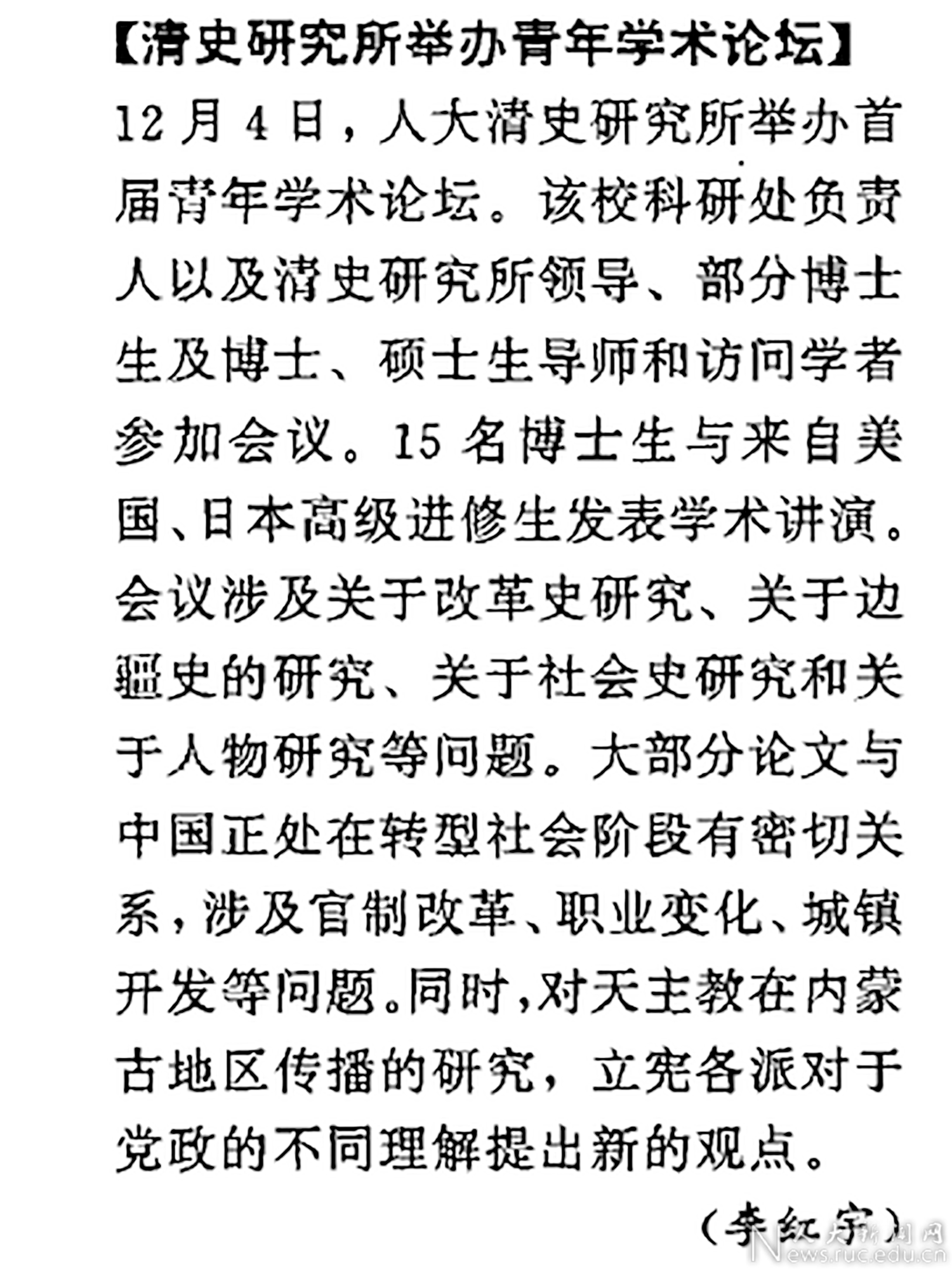
(1998年首屆青年學者論壇登上《北京教育年鑒》)

(第十三屆青年學者論壇會務組及簽名板)

(第十三屆青年學者論壇合影)
清風學社成立于2003年12月,是由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指導,學生自主創辦、以研究生為主體的學術性社團。初創時,戴逸、李文海等清史泰斗曾擔任清風學社學術顧問。多年發展,清風學社早已深深融入清史研究所這個海內外史學重鎮的教學、研究與運營的全體系當中。
先生們執杖秉燭,傳授史學、廣博史識、拓展史才、涵養史德,學脈相傳間,史學大家的精神風骨在這群年輕的學人身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記,也由此引領他們邁進浩瀚的史學天地。

(戴逸、李文海先生出席第五屆青年學者論壇開幕式)
到今天,清風學社已在中國人民大學走過了20個春秋。
20年間,這群年輕的清史學人沉醉于史學寶庫中的吉光片羽,在承載千年文明的時光隧道往來穿梭。諸子百家作伴,經史子集在側,浩瀚的星空下,他們縱一葉扁舟,以后學的眼光細細打量三百年清史的每一寸經緯,從閭巷草野到詩書禮樂,從邊疆內外到大國興亡,既體悟傳統中國集其大成,又洞察現代中國何以形成。
一年前,尹世奇成為清風學社第二十屆社長,今年夏天,又把接力棒交給了現任社長、中國史專業近現代史方向博士生石權耕。
“對歷史文脈與中華文明的傳承與堅守,讓大家相聚于此,攜手同行。”石權耕說。
在學術天地間砥礪
20年里,這里不僅走出了一批優秀的青年學者,也對他們的治學態度與學術品格產生重要影響。
2011年,如今已是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教授的趙思淵,當時還在華東師范大學讀博,他和另外兩位同學一起從上海來到北京,參加第七屆青年學者論壇。
“那是段非常美好和珍貴的記憶。”
十多年過去了,當時的細節,趙思淵回憶起來仍歷歷在目。
“會上不乏楊念群、黃興濤、夏明方等清史研究領域的資深前輩,還有學界權威刊物《清史研究》的編輯老師,如曹雯、董建中等,他們中沒有人覺得你不行,每個人都對我們充滿了期待。”
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現任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的馬子木,也曾在這里留下過一段難忘的故事。

(馬子木獲得第十屆青年學者論壇一等獎)
“像這樣由學生自主創辦又直接面向學生的學術品牌,清風學社可謂開風氣之先。”
2013年馬子木第一次向青年學者論壇投稿時,還只是個本科生。
“我當時可能確實不太夠格,參加論壇的都是些名校的碩士、博士生,但沒想到文章不僅中了,后來還在《清史研究》上發表了。”
會后,馬子木有一次在校園里遇見清史所黃興濤教授,黃老師仍記得他論文的細節,言語間滿是鼓勵與期許。
那篇論文叫《論清朝翻譯科舉的形成與發展》,發表于《清史研究》2014年第3期。
這份意料之外的驚喜,讓馬子木堅定了自己要在學術這條路上走下去的信念。
就讀碩士、博士期間,從2015年開始,馬子木曾連續兩屆獲得論壇優秀論文一等獎。博士畢業時,還是一名“90后”的馬子木被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直接聘為副教授。
第三次得獎,馬子木拿著文章專門去清史所找楊念群教授,想請他提些修改意見,那個再平常不過的下午,從文章的只詞片語到可能的學術方向,他們倆聊了近兩小時。
“在清風學社,先生們的提攜和幫助,一生難忘。”
20年,少年已不再青澀,清風學社也不斷發展壯大,一個年輕的學術共同體由此集聚。就像一枚枚光滑的鵝卵石掠過水面,蕩漾開一圈圈跳躍的漣漪。
“在這里,有機會見識同代人中的高手,同時自己也在成長。”趙思淵說。
高手過招,不光在論壇上。
清風學社有一本學生獨立編撰發行的內部學術刊物,叫《清風學刊》,創刊于2003年。刊名中“清風”二字由中國人民大學老校長、清史研究所原所長李文海親筆題寫。創刊號卷首刊發的則是史學巨擘哈佛大學教授孔飛力先生的訪談。

(《清風學刊》)
從征稿啟事、稿件遴選到專家外審、返稿修改,再到清樣校對、裝幀排版,《清風學刊》編輯部同仁們對標的,是學界公開發行的權威學術期刊。
“在編刊過程中,我不僅全面了解了學術刊物的編輯制度和出版流程,還有機會閱讀了大量高水平的投稿文章,它們大多來自于國內外的一流高校,個人的學術眼光和品位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清風學刊》主編、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2022級博士生陶志鑫說。
許多曾在這本小冊子上發表文章的研究生,現都已成長為學界的中堅力量。比如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柳岳武、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中心教授韓祥、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吳四伍、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研究院副教授李典蓉、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胡恒等都曾于學生時代在《清風學刊》上發表自己的論文。
從辦社到辦刊,這群年輕人正闊步走在學術的曠野之上。
在學脈相傳間成長
走過20年,歷史的筆墨在這一方小小的學術天地中盡情揮灑,卷首筆端,學脈綿延不息。
2022年秋季學期,幾乎每個周末,許多清風學社的成員都要在公共教學樓的百人大教室里學上近4個小時的滿語文獻課,課程內容包括滿語及其分期、親屬語言及方言簡況、滿族文字史、滿文文獻概況、現代滿語等。而主講人則是同為清風學社成員的2022級博士生唐碩。

(唐碩滿語教學)
“滿文的字母從上往下寫,字母一多就會非常長,主講師兄每次都會寫好長一串讓我們一一辨讀,讀得大家‘眼花繚亂’。”
一個學期下來,歷史學院2021級碩士研究生王天昊已快速掌握了幾乎全部的滿語初、中級語法。這對她開展清中前期政治史研究有很大的幫助。
“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有相當部分的史料都是滿文寫成的。對我而言,滿語是非常重要的學術工具。在清風滿語文獻班,我獲得了與一手史料零距離對話的能力。”
這樣由學生自發組織的課外滿語學習班已持續多年,現北大經濟學院博士后、清史所2015級碩士生張心雨在博士畢業之前一直堅持滿語教學,吸引了校內外學生包括韓國、俄羅斯、蒙古國、日本、美國、荷蘭等國的留學生參與,作為社會開展滿語教學的典型案例被寫入學術刊物中。學生自發的滿語學習,同輩之間的互相砥礪,與教師開設的“滿文文獻閱讀和翻譯”等課程恰成互補,形成了人大特色的滿文教學實踐。

(張心雨滿語教學)
清風拂過,學術的氣息撲面而來,歷史的大門由此打開。
以好奇的眼光,他們向歷史的星空望去——
看西方傳教士筆下清代中國的掠影浮光,聽隱藏在文獻里中國發展的厚重跫音,問中國傳統與西學觀念何以在晚清激烈碰撞角力,尋中國新史學的過去、現代與未來,探大數據時代史學發展之道,學術午餐會、清史文編讀書班、史學前沿系列講座……為埋首故紙堆里尋古問今的年輕學者們插上了想象的翅膀,碰撞、交融、蝶變,思想的火光在這一刻激烈迸發。

(清風學社協辦部分講座海報合集)
以堅毅的步伐,他們向歷史縱深處走去——
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新館探訪蘭臺翰墨、細數家國春秋,于明清兩朝整體歷史演進中感受歷史的溫度;在中國古代皇家陵寢建筑和園林藝術的集大成者清東陵、避暑山莊研學考察,體悟其中蘊藏的深厚文化內涵與豐富歷史資源;在中國現存規制最高的古代宮殿建筑群故宮博物院,看重檐廡殿交錯縱橫,琉璃影壁相映成趣,回望風起云涌、歷史變遷……當帙卷中的故事在歷史現場徐徐展開,腳下的田野與身后的書齋一同伸向遠方。

(在清東陵研學考察)

(在避暑山莊研學考察)
行走與思考間,學術的輪廓逐漸清晰,歷史的脈搏也愈加強勁。
清風吹過,思想噴薄而出,“新聲”響起,未來奔涌而至。年輕的人大史學人,對人類歷史與文明的探索從未止步。
20年,歷史的一隅才剛剛掀開。